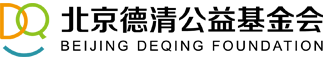无处不在的音乐,无处安放的音乐课

音乐无处不在,
校园除外。
地铁车厢里,年轻人戴着耳机,沉浸在自己的旋律中;音乐节上,人群朝向舞台,声浪如潮;直播间中,陌生人的歌声随着虚拟礼物的闪烁响起又落下;风声掠过山峦,叫卖声穿过街巷......音乐,作为人类最原始也最即兴的表达,从未像今天这样,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
可不知从何时起,最该充满歌声的地方,却渐渐安静了下来。
校园里从不缺声音。清晨的朗读声、课间的奔跑嬉闹、体育课的哨声、放学的喧哗……可这些,大多与旋律无关。音乐课的铃声响过,孩子们走进教室,四十分钟之后又安静地离开。那些音符,仿佛只是课程表上被匆匆划掉的一格,唱过,便也就此沉寂。
有学者写道:“音乐最初的形式是歌唱,因为它无需借助乐器。因此,音乐的起源亦可说是歌唱的起源。”可如今在校园里,最本真的歌唱,反而成了需要争取的存在。它排在主科之后,压在作业之下,被“不考就不重要”的现实轻轻推开。
我们享受着音乐,却似乎达成一种默契的共识:它属于生活,而不属于教育;属于天赋,而不属于努力;属于课外,而不属于课堂。
但仍有人,执意要在这片静默中发出声音。
如果你走过重庆垫江的牡丹湖小学,偶尔会听见一个女声,略带沙哑,却坚定有力。那并非清脆悦耳的音色,甚至带着岁月磨损的痕迹,但它总是准时响起,引领几十个孩子清澈的嗓音,汇成一条清晰的河流。
声音的主人叫石治英。二十六年来,她就以这样的嗓音,辗转三所不同的学校,一遍又一遍追问着:
歌声,究竟去了哪里?
而她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,很简单,也很固执——
不过是日复一日地带着孩子们,把本该属于他们的歌声,重新唱出来。
嗓音沙哑的音乐老师
石治英的声音很有辨识度。那不是人们想象中音乐老师该有的清亮甜美,而是略带沙哑,像被岁月反复打磨过。但你很快会发现,这沙哑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笃定,能稳稳承接住整个教室的注意力。
1999年,石治英从师专毕业,凭着一副好嗓子和对教育的热情站上讲台。那时的她声音明亮,对未来充满憧憬。然而现实的教学环境,却给了她意料之外的反馈。当时她面对的是八十多人的大班,没有麦克风,没有多媒体设备,只有一台需要脚踩出声的老式风琴。
“当时根本没有保护嗓子的意识,”她后来回忆,“就是嗓门大,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灌给孩子们。”课堂纪律松散,音乐课常被看作“享受课”。为了让每个孩子听清,她只能不断提高音量,一节课下来,喉咙常隐隐作痛。
不仅如此,当时石治英所在的澄溪小学校长提倡素质教育,除了常规教学,她和另外两位老师还在每周六上午免费教学生音乐特长班。
“从早上八点唱到中午十二点,连续四节课,”她说起这段经历,语气仍带着当时的纯粹。回想起来,她笑称那时“真的很单纯,也很笨”。在声音极易分散的大厅里,她带着七十多个孩子,一首接一首地唱,一吼就是四个小时。每周如此,乐此不疲。对她来说,有孩子愿意唱、有歌可以教,便是最大的满足。期末、六一、元旦,能看到孩子们登台演唱、收获掌声,她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
这副略带沙哑的嗓子,见证了她最初的教学热情,也预示了之后二十六年里,那些比保护嗓音更复杂、更艰难的持久战——当她尝试组建合唱团时,才发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
图丨石治英在城南小学上课时
留不住人的合唱团
石治英开始正式组织合唱团参赛,同样始于澄溪小学。四个孩子站成一排,穿着老师们亲手制作的苗族服饰,唱《美丽的侗乡》。那是2004年左右,互联网对小镇来说还是个新鲜词。为了这首偶尔在电视里听到的歌,她花了将近半年。她和另一位老师用刚流行的QQ,搜索“贵州聊天室”——只因知道那首歌出自“贵州苗苗艺术团”。他们在满是陌生人的窗口里一遍遍打字:“有人认识苗苗艺术团的老师吗?”
大多数时候无人回应,或者只是些不相干的闲聊。直到半个月后,一位家长偶然看到消息,他的孩子恰好在那个艺术团培训过。又经过几番辗转,一份乐谱终于通过传真机,带着模糊的墨迹,从遥远的贵州传到了重庆的乡镇小学。“等谱子就等了半年,”她笑着说,那笑容里有艰辛,也有得之不易的珍惜。
随着网络发展,找乐谱已变得容易许多,而最大的困难,始终是人。
“我一直都在重复着这一件事,”石治英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深重的疲惫。合唱团像一只破了洞的木桶,她刚用一两年时间,把三四年级选进来的孩子的声音、表情、状态打磨得有点样子,可最多参加一两次比赛,他们就升入了课业更紧张的毕业班,纷纷离队。“家长觉得耽误学习,孩子觉得训练辛苦。”大多数时候能坚持到最后的,往往是那些成绩本就拔尖的孩子。
她必须不停地招募新队员,从头开始,教他们如何张嘴、吸气、发出和谐的音。每个新学期都是又一次从零开始。她和同事一间间教室地跑,挨个问:“你在外面学过什么呀?”学跆拳道、练书法的孩子逐一被请坐,最后剩下学过声乐的,寥寥无几。大多数时候,她们得像推销员一样,向孩子们游说合唱的好处,练胆量、提气质,甚至对朗诵和语文学习也有帮助。
更难的是争取家长的支持。教书二十六年,她几乎没遇到哪位家长会主动问:“我的孩子在学校学会了什么歌?”她清楚地意识到,音乐带给孩子的自信、表达力和内在修养,是一种“看不见的力量”。“正因为看不见,所以得不到认可。我们好像一直在背后默默做事。可藏在背后做事,真的特别难。”
她大量的办公时间都被用来沟通,有时甚至像是“求人”。她得反复向家长解释,合唱不为了考试加分,却能给孩子带来体态、胆识和清晰的表达能力。她管这叫“动员工作”。最难忘的一次,为了说服家长支持孩子参赛,她从晚上六点开始打电话,一个一个耐心解释、争取,直到十点半。“还是有些家长能理解的,尤其是年轻父母,”她语气宽容里带着点无奈,“但也有一些家长,即便答应了一次,下次也很难再支持了。”
这种“不被看见”的价值,在应试教育的主旋律下,显得既微弱又奢侈。一旦孩子靠文化课就能进“尖子班”,音乐便成为最先被舍弃的选项。这种普遍的社会共识,让她和她的合唱团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、需要不断自证价值的边缘地位。

图丨合唱排练现场
她的排练永远像是在“抢人”:抢放学后的时间,抢周末的片刻。孩子们的作业、家长的接送时间、班主任的顾虑,全要一一协调。有一次为了备战市里的展演,学校特别支持让食堂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晚餐,老师们督促他们先完成作业,六点四十准时开始排练,四位音乐老师全部到位,一个指挥、一个伴奏,另外两个穿梭在孩子中间,逐个调音准、抠表情。
“其实家长也不容易,”她总是体谅地说。每晚八点半排练结束,她们得亲手把每个孩子交还给赶来接送的家长。“有一天下大雨,我回去路上真的哭了,不停地问自己:这到底是为了什么?”那一刻她的脆弱再真实不过。但哭过之后,她还是会给自己答案:“说到底,这就是我石治英该做的。”
更深的压力来自她对艺术的执着。作为教研组长,她对自己和团队都极为严格,“一件事,要么不做,要做就做好。”排练时,一句歌词反复唱几十遍,一个表情反复练到满意为止。她看得出搭档脸上的勉强,但对方出于尊重从不说什么。而这反而加重她的愧疚:“每次排完回去,我心里都特别过意不去……比完一场赛,我经常自己坐着掉眼泪。真的不容易,不是我一个人不容易,是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这种“不容易”,在2022年冬天达到顶点。那时她刚调入牡丹湖小学,肩负着为校争光的期望,带一支几乎零基础的三年级队伍突击排练。压力最大的时候,她发着近40度高烧却毫无察觉,连续三天站在排练厅里,全靠某种精神上的力量硬撑下来。
直到节目快要成型,却因为突然的疫情管控,比赛取消了。那一刻,所有努力瞬间落空,石治英却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。第二天,她又准时回到排练教室,就像过去二十六年里的每一天一样。
歌声改变的生命
对石治英来说,合唱从来不只是为了唱好几首歌。她见过太多孩子,在这个需要高度协同的集体里,被一点点地改变。
她记得一个女孩,声音条件很好,却极其内向,不爱说话。某次训练,石治英要求大家笑着唱,唯独这个女孩总是蹙着眉头,“我要求笑着唱,她却一直愁眉苦脸,我就说她影响了整体效果。”,小姑娘被说后,眼泪啪嗒啪嗒地掉,却仍站在原地没有离开。石治英没有强迫她,只是不再用目光直接施加压力,转而用余光悄悄关注。她发现,当不被直视时,女孩反而慢慢放松下来,抽泣声渐渐停了,嘴巴开始跟着一动一动,最后竟也能认真地唱完。这个女孩从四年级坚持到了毕业,后来成了合唱团里表现力最强的领唱之一。“毕业时,她送了我一个小茶杯,”石治英说着,语气柔软下来,“她说谢谢我。那一刻,我觉得什么都值了。”
还有另一个女孩,声音天生细弱,不符合合唱团的要求,却有着超乎常人的韧性。她曾在比赛前一天被换下去过,却也并不抱怨,只是默默站在合唱团的队伍里,认真地听,努力地唱。石治英有时也会批评她,她听着听着就哭了,但一边哭,一边还在唱。几年过去,当初那个声音单薄的孩子,变得异常自信。去重庆参加市里比赛后,她兴奋地分享:“站在台上,看到下面那么多评委老师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,我觉得自己很伟大,很神圣。”石治英知道,合唱给她的不只是嗓音的改变,而是一股向上的力量。“她现在变得非常有自信,还会主动帮忙收拾排练场地。我觉得她最大的收获,是学会了做人。”
这些细小的转变,才是她真正看重的东西。她常说:“如果吃得下合唱排练的苦,以后生活中什么苦都能吃下去。”在她看来,合唱磨练的不仅是声音,更是心性。它教人收敛个性、学会倾听、彼此迁就,最终在和谐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图丨石治英与学生们的合唱演出
那些曾经觉得排练辛苦、甚至哭过鼻子的孩子,毕业后却常常成为最念旧的人。他们有的上了初中、高中,还会特意回来看她,给她带信,写长长的卡片,回忆当年怎么从不懂音乐到爱上合唱。
最让她触动的是,有孩子看着她说:“石老师,小时候觉得你又高大又漂亮,现在你怎么变老了?”这话听得她鼻子一酸,却又忍不住笑起来。孩子说的是实话,却也在无意中道出一种深沉的情感——他们记住了她最好的样子,那种记忆如此鲜明,以至于岁月带来的变化让他们感到惊讶。
那一刻,石治英忽然明白了自己那位语文老师当年的心境。原来老师站在那里,本身就像一座灯塔。你无需完美,不必永远高大,只要曾真切地照亮过一些孩子的路,他们就会一直记得你身上的光。
而她,不也正走着同一条路吗?
被照亮的路
石治英心里始终住着一位老师。
那是她的小学语文老师,石志坚。不论过去多少年,每当谈起这位老师,她的语气依然会不自觉地充满敬仰,仿佛一瞬间变回了那个坐在乡村教室前排的小女孩。
“不论现在我们都已经奔四奔五的年龄了,我们同学们不论什么时候谈起这位老师,我们对他都很崇拜,很敬重。”她说。
那时候他们在农村,教学条件简陋,但石志坚老师却总有办法。没有多媒体,他就动手自制教具:一个电灯泡、一张写满生字的白纸,借助光影,把字投到黑板上。“现在回想,那就是我们最初的‘多媒体’,”石治英笑着说,眼中仍有光,“我们觉得他特别厉害,像会变魔术一样。”
但真正让她记了一辈子的,是另一件事。有一年村里突然传出谣言,说学校打的预防针会打死人,除非吃南瓜才能“解毒”。年幼的石治英虽然平时听话、成绩也好,那次却信了。打针那天,她拉着两个同学偷偷跑出学校,躲进了油菜田。“整整一天,我们没回教室。”现在回想,她才明白老师当时该有多着急。
天快黑时,她们才悄悄溜回学校拿书包。当石治英忐忑地走进教室,一抬眼,却看见石志坚老师正从宿舍窗口望着她们。原来老师早已察觉她们回来了,却一直安静地等着,没有出声惊动。直到她们快要离开,老师才走出来。没有批评,没有质问,只是平和地问:“你们去哪儿了?”看着几个吓得不敢说话的孩子,她他点头,轻声说:“要回家了?我拿手电送你们。”
他一路打着电筒,把三个孩子逐个送回家,还主动向家长解释,没有一句指责。“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一位有教育方法的老师。甚至在那个年代都不会用言语来责备我们,而他的行动其实已经把我们都感化了。”
那颗名为“教育”的种子,就这样静悄悄地落进了小女孩的心里。很多年后,石治英也成了“石老师”。她常常会想:如果换作是石老师,他会怎么做?
“我一直记得他,记得他给我的温暖,也正是他,让我一路坚持到了现在。”她说这句话时,声音很稳,也很清晰。那位老师用最朴素的方式让她明白:教育不只是教知识,更是用耐心和包容,去守护一颗颗成长的初心——而她,仍在努力成为这样的老师。
未完成的乐章
二十六年的教师生涯,石治英收获过掌声、荣誉,也见证了许许多多孩子们的成长,但她深知,音乐教育这条路,仍有太多无法弥补的缺憾。
最让她感到无力的,是那种孤军奋战的感觉。音乐老师在学校里常常是“少数群体”,甚至是被边缘化的存在。校与校之间缺乏联动,师与师之间也少有深度的教学交流。“很多时候,我们都在凭自己的经验摸索,错了也不知道,对了也没人分享。”她无奈地说。培训的机会不是没有,但大多流于形式,“听过几场讲座,学几个手势,回到学校面对的还是原来的问题。”
她清晰地感受到自身教学能力的瓶颈。合唱指挥、声部训练、作品处理……很多专业知识,是她靠一次次带队比赛“磕”出来的,而不是系统学来的。“我也想去进修,但平时课多、杂事多,周末又要带训练,根本没有完整的时间。”她叹了口气,“有时候选曲、排节目,全凭一腔热情和有限的认知,心里不是没有忐忑。”
更深层的困境在于社会对音乐教育的认知,始终没有跳出“弹弹唱唱”的框架。它似乎永远是一门锦上添花的课,而非学生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素养。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匮乏:不只是经费的投入,更是指向未来、拥抱变化的教学理念与资源的缺失。
转机发生在一次研修活动中。2023年,石治英参与了“湖光-山桥计划”支持的教师合唱研修项目。这和她之前参加过的所有学习都不一样。
“它不是简单地教你指挥手势或者发声技巧,”石治英回忆时,眼里闪烁着光,“它是在帮你转变观念,帮你看到音乐背后更广阔的东西。”项目关注的是教育观念的影响,是将音乐与生活、与人的情感、与更宏大的教育图景连接起来。她更深刻地意识到,音乐课不仅可以教孩子唱歌,更可以滋养他们的心性、培养共情能力和创造力。

图丨湖光-山桥计划音乐教育项目学习
然而期待之余,石治英以及所有和她有着相同困境的县乡老师们,也保持着清醒。大家都知道,一场学习、一个项目,无法立刻扭转积攒了数十年的观念和困境。“湖光-山桥计划”这样的公益项目能够成为一束光,为县域及乡村地区的师生们照亮一条新的路径,但路上仍有荆棘,比如覆盖面还不够广、能持续参与的老师仍是少数、以及很多基层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配备,仍难以支撑理想中的音乐教育。
这光亮虽真实,却尚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;这改变虽发生,却仍未打破所有的壁垒。石治英比谁都清楚,她所能做的,依然有限。她仍然要一次次地去动员、去沟通、去“求人”,仍然要面对队员流动、家长不解、时间紧缺的现实,仍然要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,一边摸索,一边前行。
总有缺憾。
人生如此,教育亦然。 路的尽头或许仍是路,光的后面也许还是夜。但石治英们愿意相信:正是这一点一点的补缺、一寸一寸的前行、一次一次的开口歌唱,让有些东西,变得和昨天不再一样。
她也仍会站在教室前,用那副沙哑的嗓子带着孩子们,把那些熟悉或陌生的歌,一首一首,继续唱下去。

图丨石治英与学生们
山桥后记
石治英老师的故事,是中国县域及乡村地区无数音乐教师的一个缩影。她的二十六年,是坚持的二十六年,也是在与现实反复博弈的二十六年。她让我们看到,音乐教育远不止于讲台之上的四十分钟,而是一场关乎审美、信心、合作与精神成长的漫长旅途。
山桥计划所做的,正是希望陪伴千百个如石老师这般的一线教育者,在并不完美的土壤中,持续耕耘。
我们深知,音乐教育在县乡地区面临的,从来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,而是一种结构性困境:它既是资源的匮乏,也是认知的滞后;既是教师培育机制的缺失,也是学生评价体系的单一。因此,我们并不试图以一场研修、一次活动“解决”所有问题,而是希望像石老师点亮孩子那样,去点亮老师——通过多元素养导向的活动设计、持续的资源支持、跨区域的教师学习社群,帮助老师们重新理解音乐教育的价值,也重新确认自己的职业尊严。
石治英老师说,山桥计划让她觉得自己“不再是孤身一人”。这句话,或许正是这个项目最想守护的意义。我们相信,当一位老师被支持、被点燃,就会有更多孩子被照亮;当一个班级的歌声响起,就会有一个角落的真实生命被唤醒。教育振兴的宏大叙事,正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“人”的故事写成的。
路还很长,仍有缺憾。但我们愿做那个一路点灯的人,与所有石老师同行,让更多县域和乡村的校园,重新回荡歌声、充满想象。
因为每一个孩子,都值得被音乐照亮。
每一份坚持,都应当被看见。